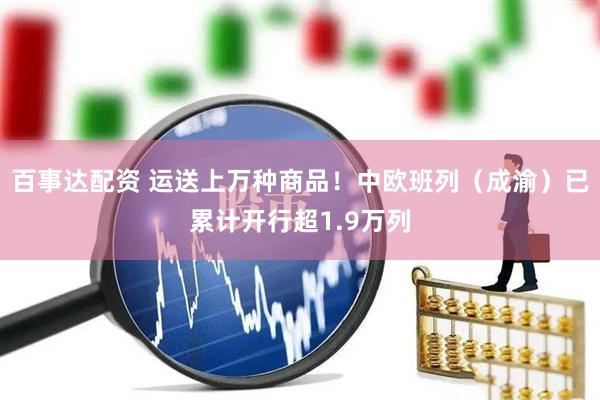1936年深秋的宿县街头汇盈策略,黄包车的车夫轻轻挑起车帘,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士从车上缓缓下车。他的衣角上带着新墨的清香,显得与周围的街道格外不协调。男子从怀里掏出怀表,熟练地检查了一下时间,随后他递给车夫两枚铜元,转身步入旁边的货栈。
那时,董士沅的生活看似平凡无奇——他在账本上简明扼要地记录着:“赏车力2角,购烧鸡1元4角,付邮汇武进家用3元。”他的日常开销,朴实而又规律。然而,谁能料到,六年后的同一时刻,这个穿着得体的商人将会在简陋的破屋中,颤抖着写下:“卖字画得银8角,购杂粮3升。”
那本日渐泛黄的账簿,悄无声息地揭示了战争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深重灾难。
体面生活的崩塌轨迹:从鱼蟹满桌到杂粮果腹
翻开董士沅1936年的账簿,里面的字迹整齐而有序,仿佛是打印出来的一般清晰。每月103银元的收入中,46元来自于他在货栈担任掌柜的固定工资,余下的收入则来自投资分红和存款利息。他的开销清单,堪称一幅市井生活的写照:每周必有烧鸡和鱼蟹,出门必乘黄包车,甚至连下乡收租时也要事先准备好开水和鸡蛋。
展开剩余75%在1936年12月2日的账单中,那笔“援绥军捐款1.34元”显得格外庄重,它印证了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在国家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。然而,这一切的转折,开始于1937年秋。
账本的空白处,突然被潦草的批注打破:“沪战起,汇武进家用倍之。”随着南京沦陷,董士沅开始频繁地将钱汇回老家,保障家人的生计。1938年初,账上不仅出现了“购爱国公债10元”与“红十字会捐款5元”,同时他对肉类的消费也有所减少,缩减了三成。
精神世界的双重沦陷:良民证与算命钱
到1940年,账本里出现了两项新支出,这让后人看了无不为之一震:一项是“办理良民证1.2元”,另一项是“算命看相3元5角”。良民证,是在沦陷区生活的百姓所必须办理的生存凭证汇盈策略,而算命看相的费用,则是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,中产阶级用来麻痹自己精神的方式。
随着战局不断恶化,董士沅的生活逐渐崩塌。在物价飞涨的背景下,他的体面生活逐渐变得难以为继。尽管他依旧坚持洗澡理发,但这两项服务已经被拆开来消费。即便他依然购买书籍,但以前他阅读的是《墨子汇海》之类的经典,战后则更多是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这些安抚内心的读物。
档案资料表明,1940年后,上海的米价暴涨了40倍,而董士沅的月收入却缩减至战前的三分之一。账簿中“邮递费”的项目频频出现,显示出他对远在江苏老家的家人的关心与牵挂。1941年某一页夹着的《申报》报道中提到“沪上名流纷纷避居香港”,而董士沅账上的一笔支出“购旧皮箱2元”则预示着他或许已经在准备逃难。然而,最终这个皮箱始终没能装满他远行所需的盘缠。
知识分子的体面:乱世中的最后防线
到了1942年2月,董士沅的账本上仍然清晰地记载着一笔“购《英汉辞典》1册”。此时,董家已经搬进了漏水的简陋厢房,但他依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。战前,董士沅的书架上摆满了《法律质疑汇刊》和《铁道史》之类的专业书籍,而战后,他的阅读书目则逐渐转向了《金刚经》与《面相学》,这也许反映了他内心的惶惑与迷茫。
与此相对应的,是当时《大公报》社论中的一段文字:“中产阶级如风中芦苇,既无劳工之无产无畏,亦无豪绅之翻云覆雨。”这句话或许揭示了董士沅面临的困境:他既不能像富商那样通过转移资产来规避风险,也无法像贫苦劳工一样“躺平”求生。在账簿上,那些不断出现的“量入为出”批注正好印证了这一点——即便是购买一瓶咸菜,他也会小心翼翼地标注下价格的波动。
恩格尔曲线的警示:生死之间的跨越
经济学家分析董士沅账本中的数据时,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:1936年时,董家的恩格尔系数仅为0.28,属于“最富裕”层级;然而到了1938年,这一数据飙升至0.605,直接跌入了“贫困”区间。这一数据的剧烈变化,正是战争对中产阶级精准打击的体现——他们既没有土地作为抵御通胀的屏障,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机倒把。
账本显示,董士沅战前的投资收益占据了家庭收入的55%,但到了1940年以后,这一项几乎完全消失。更为残酷的是,当富人通过囤积居奇来获取暴利时,董士沅这样的中产阶级却因其“体面”的束缚,无法进行灵活的转型。即使他需要变卖家当,也会选择“出租房屋”或“兼职卖字”这样看似体面的方式,而不愿像小商贩一样沿街叫卖。
这种精神上的枷锁,或许比眼前的经济困境更加致命。
发布于:天津市创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